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一起
- 知识科普
- 2025-02-03
- 37

我相信7月4日是为了庆祝我们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我们获得自由是因为大陆士兵反抗英国军队及其雇佣的雇佣兵。
所以,这也是关于士兵的。
随着假期的临近,我们会听到很多关于“最伟大的一代”的说法。我敢肯定,一些年老的战争幸存者会以一种钢铁般的眼神讲述他们的故事,当这种眼神出自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之口时,你会感到惊讶。
每个人都想成为那样的人。年轻人让自己成为二战武器和制服的专家,这样他们就可以“重现”这场战争。一些现代美国陆军制服是仿照20世纪40年代的式样设计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我的退伍军人父亲看到一个21世纪后出生的年轻人穿着“粉绿相间”的衣服,他会作何感想——绿色夹克和卡其色裤子的制服,对于那些不喜欢重演的人来说。)
所有这些都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人数可能比幸存的军人还要多。我说的是那些士兵留下的妻子和女朋友,有些人永远留在了他们身边。
我们的国家——以及我所在的阿拉巴马州西南部社区——几周前失去了其中一位女性。她聪明、风趣,而且极其聪明。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就在我和丈夫结婚前举办了一个小派对。(这是我第一次吃草莓蘸巧克力。)
她的名字叫弗朗西丝,和我一样。她的丈夫,我和他认识很短,是一个二战老兵,他会以一种非常实事求是的方式讲几个故事。当我丈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人会去拜访科尔曼一家,大人们会交流故事。
这个人的故事很可怕,尤其是因为他讲述故事的方式。他在战争期间是欧洲的轰炸机飞行员。
我丈夫很清楚地记得一个故事,而且还能重复它。
“我看了翅膀,”那人告诉他们。“上面刚刚出现了一些和这么大的洞。”他指着一个红色的圆形雪茄罐,它现在放在我嫂子的客厅里。“没有声音,只有洞。我们失去了几个引擎,我们跳伞了。”
我丈夫说,听他说话的样子,你会以为他说的是大豆的价格——作为一个农民,他对此非常了解。
“几天后我就被抓了,”那人说。“我们一天只有一个土豆,仅此而已。战争结束时,(对德国士兵的蔑称)也在挨饿。”
最精彩的部分是美国人解放的故事。他说,盟军把他们带到了一所曾经是女子学校的地方,那里是美军用来关押回国战俘的地方。
显然,粉色大理石淋浴器给这群在战俘营里没怎么洗过澡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妻子一直在等待。1942年,弗朗西丝嫁给了她的飞行员。
当她去世时,她是最后一批像我母亲一样,在丈夫上战场时等待战争结束的妇女之一。
我爱她,不仅因为我们都叫弗朗西斯,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一性别,而是因为她教会了我重要的一课。有一天,我在她家看到了她保存了这么多年的镶框军衔徽章。当我在2010年看到它们时,它们已经是褪色的博物馆藏品,但仍然鲜明地提醒着我们,我们都在一起。
当他们的爱人在军队服役时,他们的配偶、孩子、女朋友和男朋友、母亲、父亲、兄弟姐妹都分担着同样的牺牲。没有很多人为他们挥舞旗帜,这没关系;但是这些人——还有你、我和其他的人——需要记住,我们真的是在一起的。
当美国殖民地成为一个国家时,我们就在一起,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在一起。
在里面。
在一起。
现在。
如果我的朋友弗朗西丝今天能跟我说话,我想她会提醒我的。
我知道我会倾听。我希望你也会。
弗朗西斯·科尔曼(Frances Coleman)是Mobile Press-Register的前社论版编辑。给她发邮件至fcoleman1953@gmail.com,在Facebook上给她点赞www.facebook.com/prfra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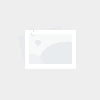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