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邪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
- 生活常识
- 2025-03-09
- 38

1961年,在参加了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后,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声称,艾希曼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他道德上的邪恶。这完全是他的常态。她在1963年出版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是“一份关于邪恶平庸的报告”。
阿伦特的这句话进入了我们更广泛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告诫人们不要再设想和实施像大屠杀这样的巨大暴行。
对于阿伦特来说,艾希曼,这个将数百万犹太男女老少送往集中营的火车的主要组织者,首先是一个高效、温和的官僚。她的论点暗示,在现代世界,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像他这样的人,在办公室里高效地工作,对事业发展感兴趣,而不是搅乱现状。
在阿伦特的艾希曼版本中,他既不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她写道,当他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法庭作证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教化”的迹象。但他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他所做的事情,包括他所参与的行动的受害者。
阿伦特写道,每当更广泛的现实威胁到自己的时候,艾希曼就会躲在行政术语和令人麻木的“陈词滥调”的墙后。她声称,正是这种“粗心大意”,使他工作得如此出色,将数百万无辜的人用精确安排的牛车火车送往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比克瑙等地。
但是,艾希曼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仍在阿根廷逍遥法外)所做的录音和手稿的全部抄本在审判后被公开,这表明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
60年前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仍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正如控方在1961年对艾希曼的审判中成功证实的那样,艾希曼并非总是盲目地服从命令。他甚至在1944年的最后几天违抗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命令,下令对数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进行死亡行军。(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希姆莱于1944年10月下令停止驱逐。)
事实上,在审判期间,《生活》杂志已经发表了艾希曼对阿根廷纳粹同志的“供词”。它取自1957年录制的70盘所谓的“萨森磁带”,总计约1000页的文字记录。
即使在这个删节版中,艾希曼也远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现的那个笨手笨脚、秃顶的职员。我们了解到,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当一切都失去时,艾希曼告诉他的党卫军同事,无论现在发生什么,他都会“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他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多“帝国敌人”的死亡。
在结束这段可怕的忏悔时,艾希曼进一步强调,他唯一遗憾的是,盟军的胜利阻止了纳粹精英在1942年1月的万西会议上“灭绝”那些注定要遭受这种命运的人。
艾希曼被耶路撒冷法院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处决。
在艾希曼审判后的几十年里,萨森录音带的完整文本已经可以用于历史评估。我们现在还有一份107页的艾希曼1956年写的政治遗嘱,题为“其他人都说了,现在我想说!”
这些文件证明艾希曼一生都是纳粹的忠实信徒。正如退休的党卫军obersturmbannfhrer(“高级风暴领袖”)告诉他在阿根廷的战友们的那样,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文员,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
“这个谨慎的官僚是由一个狂热的战士为我的血统的自由而战,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对我来说,造福我的人民是一个神圣的秩序和神圣的责任。”是的。”
在希特勒倒台十多年后,艾希曼仍然相信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大屠杀是一种正当的战争行为。简而言之,他是一个被灌输了深刻思想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达豪集中营附近和其他地方接受了意识形态训练,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来。他只会哀叹自己太过“软弱”,没有为彻底消灭德国的“种族敌人”做出更多努力。
1960年至1961年,他被“他的血亲”的死敌抓获并带到他们的圣城接受审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人尽其所能隐瞒了他在阿根廷的所思所想,并使萨森的录音带不能作为证据。“狂热的战士”也变成了隔壁笨拙的职员,玻璃后面的人,结结巴巴地做着证词。
艾希曼甚至试图说服法庭,他是一个道德普遍主义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他被一个他从未相信过的犯罪政府强迫做坏事。
那么,我们能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平庸表现,以及他如何能够欺骗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富有洞察力的哲学家,以及她之后的许多其他人中学到什么呢?
对于纳粹分子来说,正如艾希曼在阿根廷所写的那样,“自我保护的动力比任何所谓的道德要求都要强大”。考虑到“对我们的血液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与自己的种族联系在一起,普遍的道德规则,比如“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只不过是弱者用来征服强者的欺骗工具。
“不可能与具有国际性质的思想体系达成一致,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思想体系既不真实,也不诚实,而是基于一个可怕的谎言,即所有人类平等的谎言。”
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尽其所能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他可怕地撒谎,巧妙地扮演一个他认为可以安抚他的俘虏的角色。正如历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思在她2004年出版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一书中所说:
“作为伪装的一部分,艾希曼(1961年)描述自己的措辞在以前会让他暴怒尖叫。他现在是‘心胸狭窄’、‘文员’、‘学究’,一个‘不越权’的人——最后这些谎言甚至可能让他觉得有点好笑。”
艾希曼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平庸的无名小卒,他肯定也意识到,这样做会让幸存者失去一个值得发泄愤怒和愤怒的对象。任何人怎么能正当地指责这样一个平庸、无攻击性的人物,而不表现出他们自己(不是纳粹)的报复心、侵略性和不公正呢?
艾希曼在最后的陈述中甚至建议,法庭不应该谴责他,而应该承认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阿伦特没有上当,艾希曼是无辜的。她支持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然而,她认为,尽管“你(艾希曼)的内心生活和动机可能没有犯罪性质……”,他还是该死。
关于她的内心生活和这些非犯罪动机,她错了。
艾希曼仍然是一个永恒的例证,说明邪恶的特工如何利用平庸的伪装来混淆视听,转移那些想要追究他们责任的人的注意力,并继续否认他们的受害者,即使是道德制高点的微弱安慰。
当然,坏人还有许多其他的策略来试图“逃脱谋杀”。艾希曼已经在阿根廷使用了其中的几个,当他只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时,而不是为受害者及其后代辩护。
这些策略包括:首先,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在艾希曼的案例中——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他被指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大屠杀本身,在这场大屠杀中,数百万犹太人被谋杀。他们“咎由自取”,他们“让我们别无选择”,他们“完全有机会避免”,“我们还能做什么?”
其次,在行凶者的行为和受害者“已经在做”的事情之间制造了虚假的等同。阴谋论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功能,比如艾希曼纳粹主义核心的反犹太主义世界阴谋神话,就来自于创造这种想象中的道德等同。
这种对邪恶行为的指责纵容了针对敌人的政治和其他暴力,将其重新包装为自卫,即使对手毫无自卫能力。“任何能让你相信荒谬的人,都能让你犯下暴行”,正如启蒙哲学家伏尔泰所说的那样。
与这两种邪恶的合理化交织在一起的是敌人的非人化。我们在耶路撒冷外的艾希曼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反复把纳粹的受害者形容为“动物”。可悲的是,我们看到这种对敌人的非人化,今天仍在世界各地上演。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有一种犬儒主义,声称整个世界,自然本身,是一场为生存和统治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为自己,为自己的“人民”,“种族”或“国家”。这种诡辩的伪哲学是党卫军世界观的核心,植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在互联网的角落里重新出现。
它以“残酷的真理”自居,声称那些“好人”、“社会正义战士”、“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所称的“邪恶”正是世界的方式。没有人会因为做了他们认为必要的事而受到指责。正如艾希曼在阿根廷所说的那样:
“我越是倾听自然世界,无论是微观世界还是宏观世界,我发现的不公正就越少……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都是对的。”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纳粹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大门上方嘲弄地贴上了“各归自己”(To each their own)的标语。
阿伦特的书所提出的哲学挑战,鉴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并不是让我们的头脑明白邪恶是平庸的。它是重新考虑邪恶和艾希曼一直到最后都在使用的欺骗之间的联系,这一直是圣经理解的核心。
哲学家克劳迪娅·卡德(Claudia Card)将邪恶定义为对他人造成无法忍受的伤害,由明知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实施。艾希曼的案例所强调的是,对于像人类这样的社会生物来说,这样的行动通常只有通过隐藏和欺骗才能成功——除非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对称的权力。
首先是对受害者的引诱、折磨和欺骗。艾希曼的党卫军同志和他们的同伴告诉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他们将被“重新安置”,到达时需要洗澡,之后会得到食物和咖啡,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其次,在向肇事者自己辩护罪恶时,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意味:把它重新塑造成必要的、真正不可避免的、困难的、英雄般的任务,正如希姆莱在1943年10月的波森演讲中对党卫军所说的那样。正是在这里,意识形态的灌输尤其重要,尽管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宣称。
第三,隐藏行为涉及欺骗,因此外人不会发现罪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希姆莱下令,在1942年之后,所有纳粹大规模屠杀的尸体都要尽可能地挖出来焚烧,不留痕迹。在苏联人到达之前,这些杀戮设施基本上被摧毁了。
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陈腐的。要让普通人相信,对他人犯下暴行,然后隐瞒和贬低他们,是可以辩护的,甚至是值得钦佩的,需要跨越许多界限。
也许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社会,都有可能变得如此堕落,以至于在公开的战斗之外,把摧毁别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件必要的或英雄的事情。但是,如果一种有系统的谎言文化得到培育和发展,社会通常无法完好无损地生存,更不用说繁荣了。
普通的民主公民身份、文明和公共生活取决于不允许邪恶的谎言成为常态,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更好地理解他的案例在今天仍然如此重要的原因。
本文转载自The Co在知识共享许可下的对话。阅读原文。
本文改编自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今年的西蒙娜·韦尔讲座。
马修·夏普,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哲学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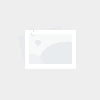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