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是奇怪和尴尬的,但我已经学会了拥抱和笑
- 作者专栏
- 2025-03-04
- 31

我已经了解我的邮递员了。白天待在家里意味着我要去应门和聊天。有时是关于天气,有时是关于我的狗,它们带着惯常的愤怒向他打招呼。偶尔,我会在街上与他擦肩而过,我们会挥手或微笑。理论上说,这很好。不知怎么的,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有一种尴尬,一种明显的紧张的高中戏剧的能量,一个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是出错,站错了位置,或者假发掉了。
邮差帕特(化名)有一次来我家不是为了送邮件,而是借了一个打包袋来清理附近一个邮筒旁边的一大笔押金。在我溜到碗柜前,把三个袋子塞到他手里之前,我们一边说着厌恶的话,一边开玩笑说这只狗一定有多大。“我真的只需要一个,小姐,”他礼貌地说,于是我伸出手来,我们的手笨拙地撞成一个塑料击掌。还有一次,他送来了一个很轻的包裹。“这是什么?”我大声地问。“感觉就像一个空酒瓶!”他回答道,我们站在那里无缘无故地吃吃笑。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诅咒。
我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不舒服但不一定不愉快的互动,以至于一个朋友形容我是“被诅咒的”。你肯定知道这样的情况:把你的借记卡放在一台机器的顶部,结果却被告知你需要把它放在其他地方,一个神秘的特定位置,每个设备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你在上厕所时,有人敲门,意识到没有普遍接受的回应。在下雨天,当你周围的人穿着更不稳定的鞋子走得更快时,你是唯一一个滑倒的人。“周末愉快!”在一个星期三。也许你也有这个诅咒。
有一天,我点了外卖,却接到了一个迷路的送货司机的电话。他向我道歉,因为他是法国人,还在学习英语,所以我深入研究了我九年级的法语课,试图用一系列的“tourner
gauche”和“aller
droite”来引导他,但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送货员在打电话,于是我喊了一声“Salut!”你好!挥舞着双臂,就像一个绝望的幸存者向头顶的飞机挥手一样。我的法语没帮上忙,但他身边的一些孩子帮了忙,他们指出有个疯女人正朝他的方向跳来跳去挥手。谢天谢地,是司机打来的,我说“非常感谢”——这次是用英语说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很重的法语口音。他收到了一大笔小费。
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些时刻会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会觉得自己又蠢又尴尬想知道是我大脑的哪一部分缺失了,让其他人在社交场合显得优雅而轻松。为这么小的事而紧张,感觉有点幼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些时刻使我们成为人类,并展示了我们是谁:我们中的一些人有点尴尬,我们中的一些人对那些尴尬的人很友好,也很理解。
没有诅咒。也许是焦虑,但不是什么险恶或重大的事情。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会告诉自己,作为一个人是奇怪而尴尬的,即使是最镇定的人也会对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说:“你也是!”在他们说“好好欣赏这部电影!”最好是拥抱和笑一笑谈论它,而不是反复思考它。不把自己当回事是不对的把我的20多岁抛在脑后真是个好礼物。我现在期待着邮递员来到我家门口,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走错一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我梦寐以求的完美流畅的社交互动——这对我来说很好。我不确定是否存在这种东西。
迪尔德丽·费奇是一名作家和社会工作者,曾为美国广播公司的《Get Krack!》《查理·皮克林周刊》和BBC。她的作品曾出现在ABC新闻,SBS,悉尼先驱晨报和弗兰基杂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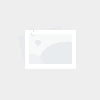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