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迪分享了他的观点
- 作者专栏
- 2025-03-02
- 34

托马斯·莫迪想让你知道他在乎你。
他担任代理海军部长的五个月于2020年4月结束,此前他解雇了受COVID- 19困扰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船长布雷特·克罗齐尔上尉,他泄露的关于船上COVID- 19情况的电子邮件在大流行疯狂的早期引发了全国的骚动。
莫德在被解雇后向TR的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引起了进一步的愤怒,有人录下了他时而暴躁的讲话,并将其泄露给了媒体,促使他辞职。
在此之前,他于2017年至2019年担任海军副部长。
莫德利的书《载体:美国海军大桥上的英雄、恶棍和心碎》于去年出版。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他对特朗普总统丑闻的看法,还讲述了他在五角大楼的生活、在特朗普总统手下任职,以及在海军部推动变革的困难。
报告显示,在部署中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在关岛停运后,莫迪建议海军高层直接检查TR,以及高层如何没有这样做。
这本书还详细描述了莫德利和他的家人在解雇克罗泽后面临的死亡威胁,以及他与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戴(Mike Gilday)发生的争吵。
近四年后,莫德利坚持他解除克罗齐尔职务的决定,并表示他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为了海军及其水兵的利益。
虽然他毫不怀疑克罗齐尔最关心他的水手,但莫迪说他也很关心。
“这是我的期望,没有人比他更关心他的船员,”莫迪告诉《海军时报》。“但我希望他的评论不是在暗示,他的指挥系统中的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比他更不关心。”
他补充说:“我们所有人都积极参与,确保船员安全,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确保那艘船可以回到海上。”“所以,我很高兴他这么想。我希望他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也要说,尽管没有人比他更在乎,但在他的指挥系统中,没有人比他更在乎。”
这位前海军军官和美国海军学院校友现在在私营部门工作,他接受了《海军时报》的采访,讨论了这本书和他领导海军的经历。
这篇采访经过了语法、句法和篇幅的编辑。
《海军时报》:今天我想以您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主题开始我们的提问:部长办公室的海军文职领导人与军中高层,特别是海军作战部长之间偶尔发生的摩擦。
这本书揭示了您与前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在您和前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的一些教育政策上存在分歧。
你也写到了在西奥多·罗斯福号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你与(前)海军上将迈克·吉尔戴(Mike Gilday)之间的一些紧张关系。
你认为这些挑战是任何领导军警海上服务的民用SECNAV所特有的吗?那些身居高位的海军上将们是否总是对他们的文职上司从军外推动的变革犹豫不决?关于这个问题,你认为可以纠正吗?考虑到文职领导对美国军事系统的重要性,它是否应该得到纠正?
Thomas Modly:嗯,这个问题有几个部分。我认为这种紧张是很自然的。我认为在我们的特殊情况下,这是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每次有政治选举或总统选举时,你都有文职领导。总统有机会在五角大楼安排大约300名公务员,政治任命人员,取代以前在那里的人。
所以,当(前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和我在2017年进入五角大楼时,那里的高级军事人员已经在那里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突然之间,他们有了新的老板,他们对什么是重要的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挑战。我不认为这是本届政府独有的。在我们的具体例子中,我认为理查森上将和我在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我认为这很好。我们在很多方面意见一致,合作得很好。我认为挑战在于发展这种工作关系。我认为对军方领导层来说,理解平民是他们的老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的军队确实是由平民控制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建立人际关系有关。我认为,我和吉尔戴上将之间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只是在TR的情况下,与我和他合作时间不长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之前,我和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比尔·莫兰(Bill Moran)一起工作,他即将成为海军作战部长。
我很确定如果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如果当时比尔是首席技术官,我认为我们建立的沟通和信任水平可能会避免我们在TR上遇到的很多问题。

NT:这本书讲述了355艘船的舰队的“白日梦”,这个舰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由网上的海军主义者推动,偶尔被智囊团提到。你不是唯一一个把它当成白日梦的人。在你看来,为什么这种白日梦一直存在?
莫迪: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一个随机的数字。我认为这背后有一些分析,得出了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同意了,但没有人愿意为此做点什么。
实际上,这背后并没有资金支持。这背后没有任何预算。当你看到海军规模的数量级增长时,不管你谈论的是什么类型的船只,海军的规模将从275艘增加到355艘。这意味着机队规模增加了35%。而且没有相应的预算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这不仅仅是船只的数量,还有所有需要的维护。所有的运营成本都是必需的。这是你需要的水手的数量,为他们提供人员和装备。这一切都是没有计划的。
当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我开始看这些计划。我知道(特朗普总统)在竞选过程中谈到了355。我看了这些计划,你看了未来几年的国防计划,它几乎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增长。在那之后,非预算知情的人数呈曲棍球式增长。哦,是的,我们可以在2045年左右把它送到那里。
这很荒谬,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问题框架。那一章我把它命名为“满是镜子的房间”,因为我谈到了人们如何能够很自在地对自己撒谎,即使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需要有人拿着锤子进来,开始打碎那些镜子,然后说,“好吧,你知道,事实是,除非我们做出一些戏剧性的改变,一些戏剧性的方向舵纠正,否则我们无法实现目标。”在我担任代理部长的五个月里,我真的试图推动这一目标,尽管遇到了一些主要的阻力。
NT:书中开头的一个主题是你试图打破五角大楼和海军部内部的模式,以及你在尝试实施新思维方式或新政策时遇到的挑战和阻力。你认为海军为什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打破常规?与此相关的是,你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还是这就是野兽的本性?
莫德利:我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如何修正和改变的例子。但这真的需要一些人非常有力地推动,一些人被改变了,他们同意改变必须到来。
你看看我们是如何发展海军航空兵的,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战舰人士的抵制,但也需要一些战舰人士真正参与进来,推动它向前发展。核海军和里科弗上将也是如此,他为推动这些项目所做的一切。所以我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我只是不认为这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我们在五角大楼没有持续的领导来做出这些改变,也没有持续的承诺。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认为他们如此抗拒是因为他们不想破坏任何东西,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压力很大,他们必须执行任务的资源有限,维护他们拥有的船只,任何类型的破坏,我认为他们担心这会破坏海军,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
但最终,为了让舰队更好地为本世纪做好准备,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NT:你写到了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空母舰,以及你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它所忍受的随之而来的延误,尽管这艘航母本月刚刚完成了首次部署。你写到了与领导层交谈,我相信特朗普总统,谈到了他对福特的失望。在福特进入市场之前,那些困扰福特的问题,你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你从这些挑战中得到了什么?与此相关的是,当涉及到一流主力舰的开发时,应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
莫迪:我认为,参与该项目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同时推出21项新技术可能是一个错误,他们可能应该在该级别的后续舰艇上逐步采用这些技术。我认为,这是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时做出的一个战略决定,目的是加快舰队的现代化和转型。
他们在那艘航母上所做的事情,我试图向总统解释这一点,我在我的书中解释了这一点,他们真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理由。增加以更高的速度出动的能力,移动加油站,转向电磁,这将允许你更快地派遣不同大小的飞机,包括[无人机]离开航母甲板,能够显着减少拦阻装置室的人员配备。能够减少你需要的人数是很重要的。我们让人冒险的人越少越好。而且更便宜。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这些都会得到回报。
但不幸的是,很多问题都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出现的,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此非常非常消极。

NT:我不知道你现在对国防采办界有多关注,但你是否感觉到未来会从福特那里吸取教训?或者这些错误容易重复吗?
莫迪:哦,我觉得有些错误很容易重复。我想我们会学到重要的一课。不过,关于福特汽车本身,也有一些值得问的好问题。至于,一旦我们通过了(未来的多丽丝·米勒号航空母舰),我们还会建造更多这样的航母吗?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在我担任代理国务卿的早期,我试图做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未来的航母会是什么样子?它会是另一个福特类,还是我们要走不同的方向?我召集了一个由外部专家和顾问组成的小组,由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担任主席,(前海军部长)约翰·雷曼(John Lehman)也在其中,我请他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参议员华纳同意为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时,他说:“如果你告诉我你不会预先决定任何解决方案,我就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回来告诉你,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再拥有任何航空母舰,你会拒绝它吗,你会埋葬它吗?”我说,“不,我没有预先判断任何事情。我想听听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不幸的是,在我于2020年春天离开五角大楼一周或几天后,他们解散了整个办公室。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四年来,我们基本上没有认真对待它,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记者:2020年初,新冠肺炎、西奥多·罗斯福号、克罗齐尔上尉,一系列事件导致您辞职。在书中有一处,你写到了你是如何建议(但没有指示)时任cno Gilday直接联系Crozier的,当时TR正在前往关岛的途中,船员们感染了COVID,船上正在撤离。
你还写道吉尔戴从未直接联系过船。听起来你并没有直接命令他这么做,但你强烈建议他这么做。你注意到他提到了对非法指挥影响的担忧。你批评了吉尔戴,或者你表达了困惑,因为他没有联系我们,你注意到你们俩对他为什么没有亲自联系飞船有过一次愤怒的交流。
你还注意到,当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也被敦促直接与这艘船接触,但他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你认为这两个穿制服的海军领导人没有像你建议的那样直接参与其中?回想起来,你认为这是对海军法律约束的一种遵守吗?你认为这是他们的政治保护还是别的什么?
莫德利:哦,我认为政治保护与此无关。毫无疑问,在我看来,阿奎里诺上将和吉尔戴上将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都考虑到了海军、军种和军舰的最大利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迈克·吉尔戴,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他向我提到,他不认为他作为首席作战官的职责是深入到组织内部,我在私营部门和军队呆了一段时间后得出的结论是那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我们有先进的通讯技术,我们可以拿起电话,我们可以使用安全频道打电话给某人,了解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当这样一艘船处于危机之中,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现在这件事已经引起了总统的注意,我觉得他有责任这么做。但他没有。所以我无法解释为什么。
当我们第一次做出派遣军舰进入关岛的决定时,我让我的参谋长立即联系了(克罗齐尔)。(我想)去那里和关岛的工作人员呆上一段时间,确保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那是在他们进入关岛的一天之内。所以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我被训练和学习的方式。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你的责任。这就是我所做的。
我只是无法说服(吉尔戴)做同样的事情。
NT:在Crozier的邮件被泄露之前,你写了另一封来自TR医疗官员的邮件,警告说如果不立即撤离这艘船,将会出现“一系列灾难性的情况”。他们警告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会有数十人死亡。
但你也写道,这些医务人员都不是传染病专家,内分泌学家或免疫学家。而且,在他们的电子邮件警告中,他们威胁要公开他们的担忧,你说这基本上相当于“医学叛变”。
与此同时,你的书也提到了事后诸葛亮。而在2020年春天,一切都非常不确定。人们,即使他们有工作要做,也有点害怕和害怕。
近四年后,你对那些医务人员是否更宽容了一些?还是你仍然觉得那是他们的一大罪过,他们只是做得太过分了?
莫迪: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不会怀恨在心,也不会原谅任何人的任何事。对我来说,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一个非常糟糕的判断错误。我认为他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不仅威胁要公开这些信息,他们还说他们会公开这些信息。这是他们在信中所说的话,他们都签了名。
那封信还说,如果我们不疏散船上的所有船员,10天内,其中50人将死于COVID。作为一名医学专业人士,我认为这是非常不专业的。所以我理解他们很担心,可能是惊慌失措,也可能是疲惫不堪。但这不是我们对军舰医务人员的期望。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和海军医学主任和CNO交谈,他们的回答是,嗯,我们认为他们只是累了,他们不是真的这么想。我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下船去找一些不累的,能处理好这事的人呢?他们向我保证,有一支15人的医疗小组从冲绳赶来,是一支海军陆战队医疗小组。所以我当时感觉好多了。
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群人在危机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对任何人怀恨在心。这是一堆情况;在这个国家,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时期。我们都陷进去了。
NT:说到克罗泽,你写到他无疑关心他的水手。你从来没有在书中质疑他对服务的奉献精神,或者他对导致这些事件的国家的服务,但你确实对他如何处理COVID爆发,泄露的电子邮件和所有这些事情提出了质疑。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你对克罗齐尔如何处理他的COVID爆发、电子邮件和后果有什么看法。
莫德利:当然,我很感激。这本书大约有400多页长,其中至少有100多页是关于TR上的COVID危机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细节,很难在简短的采访中完成。
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信任和信心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有第10条规定的责任,为我们的船只配备人员、培训和装备,并确保我们有合适的人来管理这些船只。在那一刻,我的判断是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后来我又跟他谈了一次。这是他的信泄露后的一天。他看起来很平静,说事情正在好转,他们有足够的呼吸机,船员的轮换制正在发挥作用,医院的房间现在可以使用了,等等。
于是我说,“好吧,不过是几天之后,你为什么要发那封邮件?”他说,我们刚刚拿到了一些测试结果。我认为,这批检测将新冠病毒阳性病例的数量推到了100多例。”他说,基本上,他觉得是时候发射信号弹了,或者说红色信号弹。
对我来说,这是当你的船在吃水线处下沉时你会做的事。这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求救信号。那一刻,我觉得他这么做是不合适的。
那一周,我和很多不同的人交谈,包括很多四星和其他人,试图理解,其他曾经是打击群指挥官和航母指挥官的人,他们每个人都说他的行为值得宽慰。但在这一点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关系问题,因为他被媒体宣传为一个人,引用原话,对华盛顿说真话,而华盛顿不听。
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关岛的900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到了这周的晚些时候,我和战斗群指挥官本人谈了谈,他告诉我,上尉向他吐露,他在发送邮件之前没有和他分享邮件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战斗群指挥官不会让他发送邮件。
我问战斗群指挥官(斯图尔特·贝克少将),你会让他送去吗?他说,“不,我不会这么做,他这么做是不合适的。”我说:“那你觉得他应该松一口气吗?”他说:“是的,我认为他应该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给了他压力。我是说,我是海军部长,他是一星上将,他可能觉得我给了他压力。但电话里还有其他几个人告诉我,我给(贝克)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回答。
但在那一点上,这真的不重要,因为我从海军上将那里了解到,船长是故意不服从他的打击群指挥官的。我只是觉得我需要有人在飞船处于危机的那一刻做出更好的判断。所以我决定把他换掉。
NT:如果事情没有进展,你会如何看待发出的信号耀斑邮件?你把这个框定为轮子在运动,基本上,计划在起作用,900人在关岛努力让水手们下船。在你看来,在某个时候,他在指挥系统之外发出这样的信号是合理的吗?还是你认为这是完全不允许的?
莫迪: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不认为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就像我说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订婚了。如果我们没有联系他,打电话给他,如果关岛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水手们生病了,在船上病得很重,他无处可送,他对他的打击群指挥官感到沮丧,他的直接诉求点是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
在他的邮件里,他甚至都没有发给他。他绕过他,只发给飞行员。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很明显,有些时候你必须承担风险。如果你觉得情况需要你这么做你觉得你是在拯救别人的生命,但我觉得现在不适合这么做。这是我的主观判断。
NT:你写的是2020年春天围绕克罗齐尔上尉的英雄故事。他把自己说成是为受困的水手挺身而出的船长。你提到了广受欢迎的克罗泽船长(Capt. Crozier)在获释后最后一次离开TR时的颂歌视频,以及尽管船员们都担心新冠病毒,但你让一群未戴面具的水手聚集在甲板上向他唱再见,这似乎与对病毒在船员中肆虐的担忧背道而驰。你认为为什么克罗泽的英雄故事在那几周内演变了?谁对此负责?
莫迪:我想,总的来说,这是因为他真的是个好人。我认为最基本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军官,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做了很多非常英勇的事情。他和他的船员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对我来说再明显不过了。我认为,如果他不是这样,如果他是一个暴君或魁格船长那样的人,那么这个故事就很难深入人心。
我认为,因为船员们都很爱他,他对他们很有亲和力,感觉他在尽他所能为他们做一切,我也相信他在做,我认为这有助于充实这个故事。但同时,我认为它被媒体歪曲和放大了。
当时正值总统大选。许多媒体本质上并不支持总统和总统对COVID的处理。这只是另一个机会,我认为,证明政府是漠不关心的,不关心小人物或水手。总统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因为总统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位上尉的不满。
所以我认为这有点像人为地设定了战线,但有时当这些叙事开始时,是不可能阻止它们的。
NT:我认为你的一些媒体批评,作为一个报道过其中一些事件的记者,是非常公正的。特别是,你会看到西奥多·罗斯福的后代在我们国家一些最大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克罗泽被解雇的评论文章,当时他们评论此类军事事件的资格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我也会反驳说,我们只知道我们知道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关于TR上发生的事情的更多背景直到2020年夏天才真正出来。
回想起来,你认为海军或你自己是否应该提供更多的实时反击“克罗齐尔是英雄”的叙述?
莫迪: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角度谈谈。我的意思是,我从关岛回来后决定,我不能再有效地工作了。因为国会的反应,尤其是国会的蓝派,是如此的消极。他们要求举行听证会。我面临着死亡威胁。我的家人在网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死亡威胁和愤怒。我不希望我的工作人员或团队,海军秘书处,花一分钟的时间试图恢复我的声誉或任何需要与国会或其他任何人做的事情。
我与(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就此进行了交谈。他说,“你可以把这当成你自己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你可以去说服国会议员,告诉他们一切的真相。”
我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我的时间或纳税人的时间让我去做。”我是政治任命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任命的官员是可以牺牲的。我只是觉得我留在这里试图纠正这种说法对海军来说不太好。
海军对此进行了正式调查。他们公布了他们的发现,这是吉尔戴上将想要做的事情之一。他想让船长停职,然后进行正式调查,我非常反对这个想法。我觉得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会把他停职,他会坐在关岛的某个酒店房间里,船员们仍然会把他当作船长看着,不知道海军要做什么。那么我们当时派来接替他的队长就不合法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糟糕的主意。
但(吉尔戴)觉得他可以在几天内完成调查。我在五角大楼待了这么久,知道调查不需要几天。他们需要几周,几个月。那次危机开始于4月或3月,结束于6月。所以我没说错。
调查中有趣的一点是,在整个危机期间,五角大楼里只有两个人与克罗泽上尉或攻击群指挥官有过直接接触。那就是我和我的幕僚长鲍勃·洛夫,我们两人都没有因为那次调查而接受采访。
所以我不知道。消息传出时,我正在安纳波利斯的家中,我甚至不知道(调查)会出来,他们发现他还做了其他几件事,这些事削弱了他被恢复为这艘船的指挥官的能力,而且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但在那个时候,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对我来说,最大的违法行为是在不安全的频道上发送信息。在游戏中,这一点并不重要。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会纠正一些记录。
但有趣的是,当我在关岛见到他时,我的意思是,在所有因为我替他解手而对我生气的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个觉得我这么做是对的人。当我和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告诉了我。我说:“我只是想向你解释为什么我要让你解脱。”
他说,“先生,你不必再说什么了,”或者,你知道,“我把你置于一个糟糕的秘书的位置,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也会解除我的职务的。”所以我认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错误的或不合适的,他是在冒险。
有时这些风险会带来回报,有时则不会。所以我当时不太关心克罗泽船长和他的事业,我更关心的是船上是否有一个船长,他可以照顾那些水手,冷静地管理这个过程,让船尽快回到海上。
我们最后让前指挥官卡洛斯·萨迪洛(Carlos Sardiello)负责。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半,对这艘船非常了解。两周后,船又回到了海上。所以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尽管有那么多痛苦,我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NT:你在书中写到,在克罗齐尔被解职后,你给他提供了一个海军部门的职位,作为其他船只处理自己的COVID爆发的联络人。后来怎么样了?
莫迪:嗯,讽刺的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就是我。两天后,我就走了。
当我在关岛与他坐下来时,我告诉他我相信救赎。我在书里讲了很多关于救赎的内容,以及我有多相信救赎。错误对人来说不一定是致命的。
我和每一位船长、每一个海军设施和船上的指挥官谈过,他们都有我的私人电话号码。如果你觉得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我不会报复你,直接找我就行了。和我交谈过的所有其他船长和指挥官,他们都很冷静。他们有很好的程序,就连与罗斯福同级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的指挥官也有很好的程序,似乎没有人感到恐慌。他们觉得他们从海军医疗指挥部得到了良好的医疗建议和良好的医疗照顾。
所以当我和克罗泽上尉坐下来时,我说:“我相信救赎,如果你愿意,我愿意帮助你让你的事业重回正轨。”我已经和海军航空兵司令德沃尔夫·米勒(DeWolfe Miller),也就是“子弹”米勒(“Bullet”Miller)中将谈过了,米勒在科罗纳多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说,“如果你想来华盛顿和我的团队一起为我工作,我需要有人。你是船上有新冠病毒的最老练的海军上尉,我相信你学到了很多。我需要有人每天跟那些队长说话。所以,如果你想来帮忙,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至少还需要9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我是说,这是我的预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
他摇了摇头,说:“谢谢。”但我想他知道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另外,正如我所说,作为一名政治任命者,我不知道我将在那里呆多久,能够完成它。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如果他愿意来做这件事,我会立刻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做这件事。
NT:回到调查上来。有没有人向你解释过为什么你没有被面试?
模式:不。从来没有听取过汇报。我得到的只是公共事务部门的人的提醒。
那时,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实际上写了一份声明,如果有人问我要一份声明。我写了一份声明,基本上假设他已经复职,另一份声明假设他没有复职。我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从来没有人向我要过,所以我从来没有提供过。
NT: 2020年4月6日,在你解除克罗齐尔的职务几天后,你飞到TR向机组人员发表讲话,这可以说是导致你任期结束的关键事件。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如何处理这件事?
莫迪:哦,杰夫,从一开始,我就可以用一百万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整个关岛之旅最大的挑战,我最初的意图是,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只是去看看当地发生了什么,和关岛的州长交谈,因为她是提供酒店房间的人。
然后和船员见面,在船上四处走走,就像我每次见到一艘船时所做的那样,在甲板上走走,去引擎室,和人们交谈,看看他们的感受,向船长和战斗群指挥官保证我们在华盛顿支持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真的需要他们在这一刻勇敢起来。
当负责我安全的医疗团队和海军犯罪调查局(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的人建议我,或者告诉我,我不能在船上走来走去,我需要在后甲板上的一间洁净室里向船员们发表讲话时,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犯了个大错,听信了他们的话。这是我的责任。但在此之前,我要求[TR的工作人员]提交问题,因为我希望能够回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
我想有33个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关注的是让我们离开的流程,酒店房间什么时候有空,等等。但坦率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尊重我,也让我意识到,他们没有得到有关实地情况的良好信息。
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你得到我们的帮助之前你能接受多少水手死在TR上?这是他们很多人的基调。其他几个问题是,我们不是在打仗,为什么水手会死,诸如此类的问题,这让我觉得船上的领导没有很好地沟通正在发生的事情和风险是什么。
早上,我和总督谈过,总督告诉我,船长的信使她推迟了三天才订到旅馆房间,因为关岛的居民非常害怕这些生病的水手进入他们的旅馆房间,因为她必须召回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而且他们在关岛没有那种医疗设施来应对大规模的COVID爆发。
地面上的水手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提供客房服务,来回接送水手……他们告诉我,当船长的信发出去的时候,他们的风帆有点泄气,因为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人在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们。事实远非如此。
我只是真的希望[TR水手]不要害怕。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在美国,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什么,也不知道美国的叙事有多恐惧

但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们不能让恐惧主导叙事的地方是美国海军。如果有人能处理这样的危机,那应该是美国海军。我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害怕,但他们将面临比这更大的恐惧。
有些词我应该选得更仔细些。我在《纽约时报》上对特威德·罗斯福(Tweed Roosevelt)那篇文章的回应中引用了一段话,是关于天真的。
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认为我是在说船长太天真、太愚蠢,不适合当一艘船的指挥官。但事实上,我说的恰恰相反,他既不幼稚也不愚蠢,他是故意这么做的。而且故意这样做,故意不服从命令,这违反了指挥系统和[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当我说出来的时候,事情并不是那样的,这真的是我的错。
我曾经告诫过他们不要把媒体作为他们指挥系统的一部分。然后我继续准备我在2018年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关于爱,以及他们如何真的没有责任去爱他们的船长,尽管我知道他们爱他,他也爱他们,他们的工作是爱这个国家和宪法,他们发誓要用生命来捍卫,爱和照顾为他们工作的人。
担心你的队长不是你的工作,那是我的工作。我有点像在告诫他们。有人在录我的讲话。他们立即把它发给了NBC新闻,然后NBC新闻挑选了他们想听的内容。
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坐下来听录音,说实话,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叙述是什么,我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当我听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真的不是在尖叫,而是很有力量。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冷静。但我们谈的是严肃的事。这就是那次演讲的内容。
当我离开这艘船的时候,我有点觉得,嗯,我有点错过了目标。我真的应该在船上四处走走,和人们聊聊天,但该做的就做了,仅此而已。
NT:你是否认为泄露出来的你在TR演讲的音频因为你偶尔在其中使用了几个脏话而变得更有新闻价值?很少听到一个高级国防领导人扔下F弹。
莫迪:在公共场合很少听到这样的话,但我敢打赌,你在五角大楼、一艘船、一处海军设施、一间媒体编辑室、或任何其他批评它的地方,或国会大厅里走一走,就会听到类似的话。
所以,我对此并不天真。我知道那是个错误。我没想到它会在全世界播出。对我来说,我是在和船上的水手说话。说实话,我在船上当过一次水手,直到我听到这个词,或者听到广播,我才知道我用了这个词。那篇演讲大概有两三千字。我觉得整个单词里有一个F单词和两个S单词。我想我大概谈论了15次爱情。
所以,没有任何借口,我只能告诉你,使用它不是故意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装腔作势。这只是当时说出来的话,我并不是真的在诅咒他们,我想我用了F这个词来形容高超音速导弹之类的东西,就他们应该真正担心什么而言。是的,我犯了很大很大的非受迫性错误,我无法挽回。事情就是这样
NT:这本书表明你在帮助领导海军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深刻的思考和反思。你有句话是关于我们如何用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相信的做到最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不鲁莽或不考虑别人。
回顾过去,你觉得你能把同样的恩典延伸到克罗泽,或者书中其他你认为有问题的人身上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点“后见之明是20-20″”的恩典吗?
莫德利:哦,当然。肯定的。很多人都活该。正如你所注意到的,在这本书中,我在每一章都谈到了英雄和恶棍。我认为在那一章或之前的一章里的恶棍是优雅。因为我不认为在危机的早期,甚至现在在华盛顿,任何人都在放松自己,游戏一直在进行。
所以,是的,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理解,也许我希望它能在书中体现出来,那就是我的决定,我解除克罗泽上尉职务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举动,尽管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有惩罚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有责任确保船长在如此重大的危机中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的感觉是他不是。我需要让船回到海上,我需要一个更稳定的掌舵人。就是这样。如果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指挥官,或者不是一个好人,或者一个好军官,我就不会给他机会来为我工作。只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这艘船需要一个更稳定的人。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
NT:至于当时参与其中的其他人,吉尔戴上将和其他人?
莫迪:我甚至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我原谅的,他们当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知道他们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你知道,坦率地说,当我告诉他我将做出这个决定时,我们和国防部长谈了这件事,他完全支持我。我知道他不想,但他确实全力支持我。因此,我一直对此非常感激,也非常尊重他。他的工作真的很辛苦。
我的遗憾更多的是回顾过去,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与[吉尔戴]建立长期的工作关系,事情可能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
如果我在克罗泽告诉我不要来关岛(在邮件泄露和解雇之前)时没有理睬他,我向你保证,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他知道我要来,他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写信了。我本可以在那里监视事态的发展,告诉他们事态发展得不够快,或者我本可以去见州长,做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
通常,造成这种危机的不只是一件事。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当我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想去,而他要求我们不要去的时候,我应该不顾他,直接离开。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避免。然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新冠肺炎的其他危机。我想海军关于整个TR事件的报告是在6月份发表的。我想我们对乔治·弗洛伊德和其他所有人都很着迷。所以,这是下一个危机,今天的下一个COVID危机。
尼克:轻松地说,这是地狱般的一年。
我问过克罗泽这个问题,但我也很好奇你的看法。他松了一口气,你辞职了。作为一个人,在你领导海军之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你的任期如此突然地结束,对你个人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你和你的家人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是否有一段恢复时间?或者你是否能够无缝地继续前进并回到私营部门?
莫德利:哦,我觉得你永远也做不到。大多数这样的经历都是人生的定义。你不想让它定义你的生活。但坦率地说,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我必须辞职。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我带来的人做出了很多牺牲,从私营部门来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我遇到的所有人,我遇到的所有水手,我遇到的所有退伍军人,都是难以置信的不可替代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当你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离开时,你会觉得你让他们都失望了。
当我在书里写的时候,当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们沿着14街的桥开回马里兰。我看着我的妻子,我说,“哇,我从没想过我会这样离开华盛顿特区。”我在那里待了30年。

她说:“好吧,如果你认为在这个镇上还会发生别的事情,那你就太自以为是了。”这能帮你打好基础。但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非常非常困难。但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不幸的是,我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政治和政府的本质。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我永远不会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阻止任何人服役。我珍惜每一刻。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我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困难中也总有一线希望。
坦率地说,如果我最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写这本书。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TR的,它还包括我们在海军中所面临的各种教训和挑战。希望人们能注意到它。
这些天你在忙什么?
莫迪:我正在做一些咨询工作,做一些关于这本书的事情,做一些演讲,我现在正在开始写另一本书。我只是概述了一下,很高兴能继续下去,并有一个目标,希望在夏天之前完成。我们拭目以待。完全不同的主题,与政府无关。
NT:你最喜欢的海军舰艇是什么?
莫迪:我最喜欢的海军舰艇是克利夫兰号。那是LCS 31。这还没有投入使用。但我妻子是船的担保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很自豪能够帮助影响斯宾塞部长以克利夫兰市命名这艘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认识了这么多克利夫兰的公民领袖,他们对这艘船和一切都非常兴奋。这很好。
也许第二受欢迎的是一艘也没有服役的,但我很荣幸地命名了它,它是多丽丝·米勒号,CVN 81号,我以一位非洲裔美国水手的名字命名他是珍珠港事件的英雄。
那可能是我执政以来最棒的一天。那是四年前,在马丁·路德·金的生日那天,我们在珍珠港为那艘船命名。我对这艘船的完工和服役感到非常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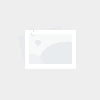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