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I正在崩溃吗?|啊
- 知识科普
- 2025-03-02
- 28

高等教育当然面临着清算——“收获旋风”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我看到哈佛大学在国际聚光灯下不安时,我发现很难表现出同情。根据我从新任临时校长那里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哈佛正“受到无情的关注”,受到“持续的审视”,这把哈佛推向了一个“极其痛苦和迷失方向的时期”。我只能诚实地说,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多年前就从哈佛毕业了,不能说我对那里的校园政治了如指掌。然而,我是一名刚从主流大学毕业的博士,我可以很容易地推断。我毫不怀疑,我过去几年在校园里的经历,恰恰反映了让哈佛陷入如此“痛苦”困境的那种恶作剧。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太高兴,但我承认,看到学术界自食其果,我感到某种满足感。
我懵懵无知地进入了历史学博士课程。我真诚地寻求一个思想共同体——一个可以自由交换思想和收集有趣知识的地方。虽然这段经历并不完全是痛苦的,但我不得不说,获得学位后我的首要感觉是一种解脱。是的,是的,完成博士学位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最重要的是还有别的东西:终于不用看自己说话的感觉,我想一个人离开政治再教育营时的感觉。别再盯着我看,别再威胁我,别再咬你的舌头。
例如,我一开始就因为试图公开谈论性别政治而遭到一群极其敏感的人的排斥。我大声地想知道,当下的跨性别运动本身是不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被告知我的问题是“暴力的”,在校园里是不能容忍的。
在我的作品集考试中,当我对长期存在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发表意见时,一位终身教授站起来命令我“不要再说人了”,只能用“人”这个词。这件事太令人尴尬了,影响了我的考试。这甚至导致一个中立的成员(一个古生物学家,上帝保佑他)向院长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投诉。当然,这一抱怨毫无结果。
几年后,我甚至都懒得申请大多数最好的奖学金机会,因为他们公开宣称“将优先考虑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我并不认为“历史上的弱势群体”指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农村人、中年人、退伍军人、不符合传统的左派……
这并不是什么启示,但对失控的“多样性、公平、包容”(DEI)思想控制的担忧日益高涨,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的任何一门课上,学生或教师都不能公开询问种族或性别问题。讨论被奴役的欧洲人和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历史?蟋蟀。性别角色的语境化,蔑视标准的“压迫”叙事?不。
多年来,我的导师在阅读我的作品时除了赞美什么都没有,但在最后一刻,他突然要求我把“Indian”(印第安人)这个词换成更讨人喜欢的词(可笑的是,西班牙语的“Indio”就足够了)。我的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对我以印第安人的名义比较记录在案的民族历史仪式表示不满,这显然是一种家长式的、不明智的做法。
听着,我不是说我很惊讶。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从一开始就怀有怀疑。此外,我很愿意承认,对我的学术经历的一些不满是我自己引起的。但是,如果忽视弥漫在现代教师走廊上的那种奇怪的、半威胁性的紧张气氛,对悠久而可敬的学术传统是一种伤害。像我这样的学生过去几年在智力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和鼓励。学术激进主义已经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才能,而且似乎执意要重蹈覆辙。
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乐观的一面。如今,在最近的记忆中,高度政治化的觉醒正统正首次受到成功挑战。象牙塔上的裂缝已经变成了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裂缝。我曾告诫那些渴望上大学的孩子们,我不会在学费上花一分钱,这似乎成为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观点。与此同时,《哈佛商业评论》(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试图解释DEI举措的急剧崩溃,现在建议公司“探索与身份中立但消除工作场所偏见的DEI行动”。例如,建立结构化的招聘和晋升流程,以明确、透明、择优为标准……”换句话说,“种族主义已经够了。”也许这种疯狂即将结束。
哈佛对外界审查的高度愤怒就是一个说明。尽管在被追究责任时出现了所有“痛苦和迷失方向”的混乱,但这一信息似乎正在传递。临时总统告诉我们,“在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致力于自由探索和表达,这一点从未如此重要。”坚持对学术卓越的最高承诺从未如此重要。追求真相从未如此重要。”确实。也许,面对的清算将开启它迫切需要的长期航向修正。也许它甚至会回到我希望去的那种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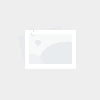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