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恳求我的医生找出我到底怎么了相反,我是医学上的煤气灯
- 知识科普
- 2025-02-27
- 31


我丈夫和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和我的婆婆视频通话,她是新德里的一名医生。我们的谈话通常都很轻松,但有一天早上,她想和我讨论一件更严肃的事——我的健康。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谈论我是如何在感染COVID-19后与致残的慢性疾病作斗争的。她认识不同专业的医生,并问她是否可以把我的化验结果分享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获得非正式的意见。我同意了,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也许他们会发现一些别人错过的洞见。
几周后,在2021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的岳母带着灿烂的微笑加入了视频通话。她从她的医生朋友那里听说了。
“好消息!她说。“他们看了你的实验室和病史。事实证明”——提示鼓声——“你没有任何问题!注意健康饮食,每天做瑜伽,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的心一沉。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谈论我的症状,这些症状使我无法工作,有时甚至无法起床,但我自己的家人不相信我生病了?我不想冒犯她。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感谢她的努力,然后保持沉默。电话结束后,我哭了起来——不敢相信连她都不理解,也为自己表现得如此沮丧而感到羞愧。
自2020年3月以来,我一直患有COVID。我的病让我亲眼目睹了慢性病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被解雇的情形。医生们一再怀疑我的症状的真实性,让我一年多没有得到治疗。可悲的是,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长COVID的患者“描述了遇到无视他们经验的医疗专业人员,导致漫长的诊断过程和缺乏治疗选择。”他们经常将这种互动描述为“煤气灯”,即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后又被怀疑的令人抓狂的感觉。
歧视似乎推动了这些动态。对于许多患有慢性疼痛和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等疾病的人来说,对COVID - 19的广泛忽视是一个熟悉的故事。患者通常要挣扎数年才能得到诊断和治疗。ME/CFS是一种与COVID类似的疾病,可能由单核细胞增多症等感染引起,它的历史特别丑陋。

许多患有严重ME/CFS的人已经等了几十年,直到医生认真对待他们的症状。与此同时,他们的生命在黑暗的房间里消磨殆尽,因为病情最严重的病人无法离开床,也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吃饭、洗澡、上厕所——没有全天候的帮助。大约90%的ME/CFS患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仍然没有被诊断出来。Long COVID与这一悲剧相呼应,尽管与ME/CFS患者相比,该疾病患者受到的忽视较少。
像许多患有COVID-19的人一样,我的病始于COVID-19的“轻度”病例。医生说这种感染“7-10天就会痊愈”。我躺在床上等着。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症状并没有好转;它们只是在变化。我不再感到呼吸急促,但开始“看东西有困难”,正如我所说的我的眼睛疲劳和对光敏感。
我的主要症状是极度疲惫,而且越来越严重。这种感觉不同于睡眠不足或工作过度。更确切地说,这更像是头部被蝙蝠击中的后果:持续的头痛,眼睛无法聚焦,光和声音引起的疼痛,以及我需要蜷缩成茧,等待疾病过去的感觉。大约一个月后,我几乎下不了床。我会在昏暗的房间里躺上几个小时,望着窗外的一片天空。
我开始直觉地明白,我的病可能是长期的。有一次,我瞥了一眼手机的背景:一张我在上一个劳动节在缅因州徒步旅行的照片,参差不齐的岩石和松树张开,露出一片广阔的蓝色海洋。绝望开始爬进我的胸膛,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无法不被一个衰弱的身体所拖累而在大自然中行走了。我告诉所有人——我的家人、医生——我担心我不会好起来。他们说了各种各样的“是的,我知道你有这种感觉。”
重病大约六周后,我非常想找一位专家谈谈,他能给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找到了一位初级保健医生,告诉了她我的故事:我每天下不了床超过30分钟就会感到身体崩溃。我的眼睛很难聚焦。暴露在正常的光线和声音下会让我头疼、恶心,而且会让我感到恶心。
她听了几分钟,然后带着一丝微笑说,我的症状是由焦虑引起的。我承认我很焦虑,因为我没有恢复过来。但焦虑会导致眼睛无法聚焦吗?“是的,”她带着同样的半笑淡淡地说,就像在对一个倔强的孩子说话一样。
五个月后,我去看了一位神经科医生。这一次,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她说我的症状很可能是“对大流行创伤的理性反应”。换句话说,我感到焦虑或沮丧。
就连我的心理医生也在好几个月里不相信我生病了,给了我糟糕的医疗建议,我现在认为她没有资格提供这些建议。她确信我的症状是由强迫症引起的。根据她的逻辑,我沉迷于监控自己身体的感觉,这让我错误地相信,我几乎无法下床。在我的初级保健医生说我的症状是由焦虑引起的之后,她告诉我不要和医生说话。她说:“尽量少关注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生活。”
任何熟悉新冠肺炎或类似疾病的人都知道,我的治疗师让我忽视症状的建议注定会以灾难告终。将长冠状病毒病作为心理障碍治疗是疏忽和危险的。病人被提示要“克服”他们的疲惫,这可能会使他们的疾病更加严重。
即使没有支持,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也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病情,病情好转到可以重返全职工作。然而,在数周的过度工作和家庭压力之后,我的健康状况在2020年10月再次崩溃。我又几乎卧床不起了。
从那以后,我的病情得到了缓慢的改善,但两年多过去了,我的病情仍然比撞车前更严重。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和我的治疗师谈了谈,并强调说:“我并不焦虑。我的焦虑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感觉糟透了。”她叹了口气,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回答说:“好吧,是的,去找人看看。”她没有为自己的大麻烦负责。她没有道歉。不久之后,我找到了另一位治疗师,他认为我病了。
许多专家认为,对慢性病的怀疑根植于性别歧视,这在历史上一直弥漫在医学界。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史蒂文·菲利普斯博士和米歇尔·威廉姆斯写道:“如果过去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他们(长COVID的患者)将被医学界的许多成员怀疑、边缘化和回避。”作者说,长COVID对女性的影响不成比例,这可能会加剧这种漠视。他们写道:“我们的医疗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将女性的症状最小化,并将其视为心理疾病而不予理睬或误诊。”
我的经验表明,医疗歧视确实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医生断定我的病并不存在,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诊断或治疗。我的性别可能让我更容易被忽视,因为女性一直被贴上“歇斯底里”的标签。当我面对这种虐待时,我有时觉得人们的偏见比我的人性更重要。

在一年多没有接受医疗护理后,我终于看到了两位感染后疾病的领先专家,他们诊断我患有长COVID,以及许多相关疾病,如自主神经障碍、小纤维神经病变、肥大细胞激活综合征和原发性免疫缺陷。
在我岳母试图寻找答案之后,我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测试,结果显示我的免疫系统失调,这意味着我既免疫功能低下,又患有慢性炎症,不断伤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系统受损,血液无法有效循环,导致慢性低氧缺氧。有证据表明,我的身体不能有效地从血管中提取氧气,我的线粒体也受损了。
我最终说服了婆婆我的病是真的。去年夏天,当她拜访我和我丈夫时,我和她就新冠肺炎——研究和我的实验室测试——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这一次,我的论点似乎取得了突破。我丈夫说她后悔她最初的反应,现在全心全意地相信我的病很严重。
然而,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之战仍在继续。我经常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疾病被最小化或忽视。Slate最近的一篇文章宣称,“长冠肺炎既不像最初担心的那样常见,也不像最初担心的那样严重。”埃德·勇(Ed Yong)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明显驳斥了这些说法,他说:“曾经完全否认long COVID存在的人已经变成了(一种信念)……长期以来,COVID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常见和严重——这是一小群重病患者的悲剧,但不是引起社会关注的原因。”
新冠肺炎并不罕见,而且往往很严重。研究发现,在基因组变体传播期间首次感染COVID-19的人中,有10%在6个月后患上了长冠状病毒,约四分之一的长冠状病毒感染者表示,他们的日常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患有常见相关疾病的人,包括自主神经异常和ME/CFS,预计会经历终身症状。我就是这些病人中的一员,我知道其他人也一样。
在我生病之前,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可以在办公室工作10个小时,晚上出去喝一杯,然后第二天再来一次。现在,我以前的通勤方式可能会让我自己垮掉。在我需要休息之前,我可以工作5个小时。(我说的“休息”是指“闭着眼睛躺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如果我超出了自己的极限,或者在嘈杂的地方呆了一段时间,我就会感到恶心、注意力不集中,还会出现头痛。

今年5月,我参加了姐姐的毕业典礼,那是一场两个小时的典礼,充满了冗长的演讲和激动人心的尖叫。我戴着耳塞,但离开会场时仍然感到疲惫和痛苦。我下午4点上床,戴上眼罩,直到第二天才起床。我的姐姐,她理解,让我毫不犹豫地离开。我并不总是那么幸运。当我告诉朋友我需要休息或取消计划时,我经常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到礼貌的沮丧。
一些沟通上的差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长时间的COVID或类似的疾病。这些症状大多对其他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他们只看到像我这样的人经常休息,如果他们看到任何东西的话。我们的社会没有语言来解释这些疾病。医学术语,如“劳累后不适”,指的是精神或体力消耗后的严重疾病和疲惫,听起来更委婉,而不是描述性的。
然而,即使许多人发现很难理解COVID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长期感觉,也不难理解患者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从未患过高原反应(一种因难以适应高海拔而导致的疲劳、头痛和恶心的症状),但我从未怀疑过它的存在,也从未听说过有人这样做。那就太奇怪了。
同样,色盲的人可能会接受其他能感知颜色的人的话。慢性疾病是同一类型的情况,除了它带有广泛的耻辱。就在去年,这种怀疑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长COVID的医生被同事解雇。大多数怀疑我患病的临床医生都是女性,这表明导致这些偏见的性别歧视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往往没有被认识到。
在我生病之前,我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煤气灯照明。我很容易告诉自己,大多数人相信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可信的。现在我意识到他们常常偏向我。我向有特权的人展示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世界:一个没有威胁的地方,一个自力更生和机会永远存在的地方。
朱莉·斯特拉克是一位健康传播专家和作家我住在纽约。她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年会上介绍了关于健康包容性的原创研究,并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患者-提供者参与的文章。朱莉自2020年3月以来一直是长冠患者。通过她的推特账号@juliestrack联系她。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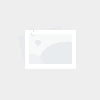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