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的真实身份隐藏了几十年以下是我终于在63岁时展示自己时发生的事情
- 百科大全
- 2025-02-16
- 31

我从没想过我会在这里。然而就在几个月前,63岁的我公开了自己是一名跨性别女性。
首先,我很清楚在美国有一种文化期望,一旦你到了401(k)计划成为现实而不是理论的年龄,你剩下的最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是看看哪个先关闭——你的动脉还是你的大脑。这应该是开始思考结局的时候,而不是开始的时候。考虑到这一切,我意识到,任何人都不太可能去做也许是最大的事情:性别转换。
更糟糕的是,我是在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候做这件事的,有太多的总统候选人和团体,他们的名字里有“自由”和“自由”这样的词,把像我这样的人变成了他们的政治pi?atas。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在尝试一些反常的刺激。然而,变性人可不像尝试刘海。它不是你涉猎的东西,然后长大就不再涉猎了。这是一种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试图忽视的感觉,直到我们要么在恐惧和沉默中死去,要么决定活得完整和快乐值得人们讨厌我们。
从我七八岁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弄清楚该做出哪个选择,我经常梦见《魔女》里的塔比瑟要和我一起出去玩。我得先把这个布丁似的东西放在小纸杯里吃。我顺从了,突然间我变成了一个小女孩,我们就出去玩了。
几年后,我开始做另一个梦,梦见我长出了能飞的乳房。还有一个梦,我觉得超级痒,当我挠自己的时候,我的皮肤脱落了,发现我看起来就像奥利维亚·牛顿·约翰。
当时,我没有质疑过这些梦想。我只是一觉醒来就觉得完整和满足,直到我稍微长大一点,学会了用一千个太阳的热量来恨自己,因为我不可能是一个女孩。我试着遵从社会告诉我的:当然,我们天生就有隐私部位。当然,性别焦虑症意味着我是一个邪恶的美容师恋童癖。当然,跨性别女性只是渴望玩洋娃娃和穿妈妈衣服的同性恋男孩,而跨性别男性则有强迫他们看足球和修理化油器的父亲。事实就是事实,对吧?
然后是青春期,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当其他初中男生对《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泳装特刊上的模特垂涎欲滴时,我却因为看到那些美女穿着湿漉漉的比基尼而深感沮丧,而我永远也穿不上。
我想我可以通过偷我妈妈的避孕药来解决问题。我吞下了一个,但我没有经历什么神奇的转变,而是直接把它吐了出来。还有一次,我从妈妈的一本杂志上订购了一个化妆包。这是一个我没有仔细考虑过的计划,因为当它到达时,她问为什么要寄给我,我说这可能只是某个恶霸的恶作剧。
我不能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家属于中西部那种传说中冷漠的家庭——“生活是用来忍受的,而不是用来享受的”,“上帝从不犯错,所以保持安静”。另外,在我高中四年的时间里,我们搬到了三个不同的城市,我没有亲密的朋友可以敞开心扉。

这种孤立确实提供了一个好处: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最后都会在当地的图书馆闲逛,寻找任何书籍或杂志文章来解释我的身体和灵魂之间的这种脱节。好消息是什么呢?纵观历史,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坏消息呢?我读到我的感觉是一种幻觉——一种精神疾病,我需要被说服。
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没有医生能治愈,我每天晚上都祈祷外星人会炸毁地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这些“变性”的想法了。自杀是一种罪恶,而不是一种选择,所以忽视这些感受是唯一的选择。
然后,我发现了克里斯汀·乔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她是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个成为美国媒体轰动人物的跨性别女性。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世界对我的看法和我对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所带来的指责和羞耻。三周后,我收到了她的便条,向我保证我不是怪胎,我必须相信自己的感觉。她还给了我一本她签名的自传,我把它藏在枕头底下,多年后反复阅读。
尽管有过短暂的满足感——比如有一次,我在一次广播节目比赛中赢得了弗利特伍德麦克女队的“谣言”t恤,并自豪地穿着它去上学,尽管我受到了无情的嘲笑——但我试着忍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女性情感带来的自我厌恶。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去见了当地同性恋中心的咨询师,在那里我被告知:a)我听起来像是一个典型的易性癖患者;b)我才17岁,所以没有人能帮我。自然地,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一种信息上,以证明掩盖所有跨性别想法是合理的。我用我能想到的任何能激发睾丸激素的活动来代替它们——找一个女朋友搬去住,边喝啤酒边不停地谈论体育运动,和哥们一起玩几个小时的吃豆人,从不和任何人深入交谈,也从不问路。
这个决心一直持续到我21岁的时候,当时我去看了一位治疗师,他只用了不到50分钟就告诉了我一些我不想听的话:我和他见过的所有病人一样是变性人。他让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了小剂量的雌激素,看看它是否能帮助我恶化的抑郁症。它做到了。然而,当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东西时,有趣的是,我的“忍受”本能把“享受”踢到了路边,我冲走了我的拯救理智的荷尔蒙,以阻止所有这些胡说八道。
在接下来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专注于寻找作为记者和制片人的成功。我结婚了。我们有两个孩子。我尽力去参加每一场棒球比赛或学校演出。我很努力地交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然而,烦躁不安的情绪就像我的大脑是一个弹球机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响。

离婚后,我偶尔会蹑手蹑脚地走到过渡线上。我会找一个新的治疗师,重新开始分泌激素——然后惊慌失措,停止分泌。我在洛杉矶LGBT中心的跨性别休息室为年长的跨性别女性教授写作课。我开始关注我在社交媒体上能找到的每一个受欢迎的变性女人,假装我有一个社区。
然而,我内心深处的跨性别恐惧症,就像loveboy音乐会上的《为周末工作》(Working for the Weekend):不可避免。转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平等的、相反的、试图把事情搞起来的尝试。我让医生给我开了睾酮贴片。我做了抽脂手术,以消除雌激素给我带来的“男性乳房”的痕迹。我成了Match.com上的约会机器,尽管大多数喝咖啡的约会都以女人告诉我虽然我看起来很好,但我似乎也隐藏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而告终。
我已经听天由命地过着我的余生,就好像我的余生属于一个我发过几次邮件但从未真正见过面的人一样,但接下来的12个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一切。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我的女儿刚刚开始工作,所以他们显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找到了生父的家庭录像,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所以除了他的一些照片外,我什么也没见过。我60岁了。当时有一场流行病,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隔离和沉思。
当这一切发生冲突时,我很难忽视自己最终要照顾好自己的愿望。我知道我需要接受我的变性,让别人知道我的秘密,否则我就会在没有享受的情况下死去。所以我寻求帮助。
我是日间电视脱口秀的制片人。当我开始考虑是否再次使用雌激素时,我碰巧和莎朗·斯通一起工作。在我们详谈了真实而无悔地生活的重要性两周后——她在这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重新开始了激素治疗,再也没有回头。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衣橱更女性化时,我上网发现了一家帮助变性人通过时尚选择找到真实自我的公司。虽然从我们最初的接触到我们的第一次购物之旅花了我六个月的时间,但公司老板Annaliese Cherry非常热情和鼓励,她说服我做了一件我从未想过自己敢做的事:和她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穿裙子。
当我要面对我最大的恐惧——告诉我20多岁的孩子们我是变性人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我早该知道他们这代人更愿意让人们做自己。
当我准备在工作中开始出柜的过程时,我向节目主持人的发型师罗伯特·拉莫斯(Robert Ramos)坦白了一切。听到我的消息后,他无限的热情——更不用说他给我剪的惊人的发型和高光——告诉我,自尊可能真的像宣传的那样。

当我想把Caragh(我为自己取的新名字,因为它在盖尔语中的意思是“心爱的”)介绍给我们赛季结束派对上的其他工作人员时,他们立即给予了我无尽的支持。几乎每个人都问我的代词和我的名字怎么读。我们感同身受的主人告诉我我的腿有多热。多年来,我一直害怕别人对我的反应,结果告诉别人我是变性人,就像告诉别人蓝色是我现在最喜欢的颜色一样,给我带来了创伤。
我很幸运生活在一个跨性别同盟存在的地方,工作在一个跨性别同盟存在的行业,但我的新生活远非完美。如果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盯着我笑,我就会溜走,因为我担心自己看起来像我爷爷穿着贝琪·约翰逊的衣服。当我翻看关于美国跨性别仇恨的故事时,那些很可能从未真正与跨性别者交谈过的人,我又哭又喊,开始谋划如何回到那个衣橱里。
然后,在黑暗中,我会在健身房被“女人”,或者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杂货店说我的衣服让我成为那里最酷的女人。或者我交到像艾米和凯瑟琳这样忠诚的新朋友,她们从未见过以前的我。这些经历清楚地表明,变性从来不是“转换性别”。相反,它真的是关于最终体验自我价值,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在阁楼上看着它,不仅相信别人,而且相信自己——这些都不是我63岁时想要做的。
我想我应该感谢所有那些说“为了社会的利益……”跨性别主义必须从公共生活中根除”,或者跨性别孩子的父母应该“从后脑勺上开枪……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们挂在桥上。”说实话,是他们的花言巧语最终促使我出柜的,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的哗众取宠继续妖魔化像我这样的人。
尽管我正处于皮肤开始松弛和皱纹的年龄,但在这种欺凌面前,我的皮肤也变得更厚了。一旦你过了60岁,你内心的“做爱计数器”就归零了,所以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我只有时间让别人看到,成为你一直想成为的人永远不会太晚。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自己的路,但现在我找到了,沿着这条路走似乎很适合我。最近,我和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喝酒。几分钟后,其中一个盯着我,朝我的方向挥手,说:“感觉就这样。”说实话,我从没想过我会听到这句话。现在我来了,这不仅仅是一场梦,我只希望现在和塔比瑟约好一起玩还不算太晚。

Caragh做恩利并不孤单她隐瞒了自己的年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她从事写作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人物》杂志、《电视指南》、《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艾美奖杂志》和《名利场》等媒体工作。她是《不能约会:当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时竞选总统》一书的作者。除了她的印刷作品,她还在VH1的“音乐背后”,“皇后拉蒂法秀”和“马丁短秀”等节目中担任制片人。她目前是“凯利克拉克森秀”的高级制片人。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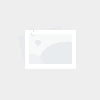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