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廉价的外国护工的悲剧性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 知识科普
- 2025-02-12
- 34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名罗马尼亚护工,在萨默塞特郡的一所房子里,你刚刚发现一位老妇人,她的头被困在楼梯电梯里,呼吸困难。那位女士是你的责任,你不应该丢下她不管。
她已经91岁了,患有痴呆症,视力不太好,但你却看到了——可能是因为别人需要你的关注。你让她一个人待了五分钟她想自己爬楼梯却摔倒了,现在她被困住了。
你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异国,你很恐慌,所以你打电话给你的印度同事,让她过来帮忙,但她也很恐慌,你们两个英语都说得不好,所以你们无法真正交流。
你知道你需要拨打999,让医护人员来,你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这位女士“被堵住了”,但他们听不懂,此外,你不确定“警觉”和“活着”或“呼吸”和“流血”之间的区别,所以当救护车最终到达那里时,老太太已经死了。在你的监视下。
难以想象的糟糕。她是你的责任。她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你离开了她,然后你又让她失望了因为你无法让别人理解你,这就是后果。都是你的错。然后你必须告诉她的女儿,她的母亲去世了,但是,你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你刚才说“你妈死了”,你知道这很钝,但你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方法说出来,因为你没有通过安全英语语言测试,所以你不是技术资格在英国工作,但没人检查,他们需要有人来做这项工作,所以他们给你。
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对芭芭拉·莱梅尔来说太可怕了,她去年8月被困在楼梯电梯里去世了。她的家人非常痛苦,他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她是养老院唯一一个住在一楼卧室的人,尽管她不能自己走楼梯或楼梯电梯。

我可以想象,这也让相关的护理人员感到痛苦,他们的职责是为这些最脆弱的公民提供关注和安慰。
但现在,这也是一个有益的故事。因为在围绕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新移民计划的众怒中,有一件事格外引人注目。
这并不是说技术工人签证的最低工资门槛跃升至略低于4万英镑。而是卫生和护理工作者不受涨价影响。
这意味着罗马尼亚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其他外国工人将继续以26200英镑的最低工资来到英国,因为他们不被归类为技术工人,不管我们有多需要他们的技能。为此,他们每月将赚1765英镑,或每周407英镑。
你可能会说,还不错。一星期四百镑!或者十分钟左右——一小时。基本上是最低工资。
那么,为什么没有英国人愿意这么做呢?相反,为什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乐于进口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这是最便宜的合法劳动力——来照顾我们最脆弱的公民:一边是我们的婴儿和幼儿,另一边是我们的老人和奶奶,来填补社会护理体系的巨大缺口?
因为我们英国人知道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多少回报。是擦屁股和清理呕吐物;它是给那些脾气暴躁、困惑的老人换床单、给他们吃药,这些老人既孤独又经常受到惊吓,所以很可能是粗鲁和困难的。
它帮助刚出院的人适应新的、受限制的日常生活。就是连五分钟都不能离开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老太太,以防她走神,试图操作家用机械。
它是照顾别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雪上加霜的是,家庭签证的最低门槛提高了一倍多,达到3.87万英镑,这意味着,如果你准备来英国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你不一定能保证自己的家庭生活舒适)。
是的,你需要说基本的英语水平,但是这份工作本身是不合格的——尽管你需要做很多培训,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很多知识。而且工资很低,而且很无情,因为总会有人需要照顾。
这才是真正的愤怒:这是关于那些需要照顾的人。这是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它不是在乐购(Tesco)堆放货架,也不是打扫办公室,在那里你可以工作几个小时,拿到工资,然后回家,把工作抛在脑后。你要对人们的生命负责——正如阿什利之家的悲剧所说明的那样。
但是,护理工作的最低工资,以及我们愿意让廉价的外国工人来做这些工作——甚至对他们是否会说我们的语言视而不见——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说的是,我们没有重视社会护理。
我们不想知道——或者至少,我们不想去看。我们不想去想我们的护理人员所面临的现实,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承认,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应该自己做这项工作;在我们选择是否想要或需要外包之前,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做的。
有一场真正的关于护理的辩论——它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我们希望它促进什么。例如,我们是否希望那些照顾我们的家属——我们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亲戚——的人这样做是为了让其他人腾出时间去工作?这是为了润滑经济引擎的更宽的轮子吗?让廉价劳动力来做护理工作,然后那些有能力从事高薪专业工作的人就能赚得更多,最终,这些财富可能会涓滴流下。
还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护理系统为我们最小的公民提供最好的结果,给我们最年长的人最大的尊严?因为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意味着我们要尴尬地讨论我们想让谁来做这项工作,以及我们准备付给他们多少钱。
不幸的是,这两个系统基本上是不兼容的。例如,如果你想让更多的女性工作,你就需要提供几乎24小时(或者当然是醒着/工作的时间)照顾小孩,并且能够把你的亲戚放在一个家庭中,当他们年老并有类似的需求时,他们也能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让孩子们得到最佳的结果,或者舒适、有尊严、有爱心的临终关怀,把责任推卸给收入最低的外国工人并不是真正可行的方法。芭芭拉·蕾梅尔的结局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那些护工听不懂英语到底是谁的错呢?因为他们敢于在别国工作?还是我们的,允许他们不顾一切地来做这项工作,因为坦率地说,他们愿意这么做?
不可能每一个有依赖亲戚的人,或者有额外需要的人,都辞职在家照顾他们。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他们这样做。例如,患有痴呆症的人需要高水平的护理。指望他们的亲戚独自处理这些是不合理的。
但克莱维利的裁决,在一场打击移民的行动中,被宣传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净移民减少,是一种默认的承认,即我们没有给护工适当的报酬,也没有充分重视他们为我们其他人提供的便利。
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更多像芭芭拉·赖梅尔那样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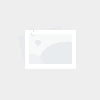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