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政治转向右翼
- 百科大全
- 2025-04-10
- 50


在安静的荷兰村庄Sint Willebrord,教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欢迎所有人”。在这里,邻居们站在整洁的门廊上,俯瞰着修剪整齐的草坪,互相问候。
但这种宽容的宣言似乎不合时宜。
由于经济和文化上的焦虑加剧了对移民的恐惧,村里和整个荷兰的人们在政治上都转向了极右。这是整个欧洲大陆都能感受到的一种趋势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趋势可能会影响今年欧盟议会选举的结果。
在圣威尔布罗德,9300名居民中几乎没有移民,在去年的选举中,几乎四分之三的选民选择了一个极端反移民、反穆斯林的政党,这粉碎了荷兰作为一个热情、温和国家的形象。
自由党由一个名叫吉尔特·威尔德斯的满头头发的煽惑分子领导,在一个穆斯林人口不到5%的国家获得了近四分之一的选票,该党的口号是“不要伊斯兰学校、古兰经和清真寺”,“不要开放边界,不要我们负担不起的大规模移民”。
欧洲各地的选民越来越多地支持威尔德斯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承诺限制移民,并在某些情况下限制民主自由:宗教、言论和抗议的权利。
这些力量在不同程度上一次在一个国家兴起,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和奥地利。但专家们担心,不久之后,他们可能会从上到下戏剧性地重塑非洲大陆。
今年6月,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将选举下一届议会,任期5年。
分析人士说,极右翼政党准备获得席位,并对欧盟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些政策涉及公民权利、性别问题和移民等方方面面。
海牙智库Clingendael高级研究员Rem Korteweg说:“人们要对‘旧政治’进行报复。”
在一些欧洲国家,向右的转变已经开始蚕食民主的基础。
民主专家说,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最近的选举是自由的,但并不公平,因为执政党控制了媒体、法院和选举当局。
自2021年荷兰大选以来,对威尔德斯自由党的支持增加了一倍多。怀尔德斯获得23%的选票,很有可能领导未来的执政联盟。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荷兰各地的选民越来越不满,因为历届政府——尽管税收水平很高——都无法阻止公民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方面的期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遭到侵蚀。
80岁的圣威勒布罗德居民瓦尔特·德容说:“就好像人们是被迫投票给威尔德斯一样。”德容一生都是面包师,他说,由于成本上升和政府严格的规定,他去年被迫关闭了自己的生意。
荷兰生活水平的下降与移民的增加同时发生。
20年前,荷兰的移民净流出,但到2022年,这个1750万人口的国家涌入了22.4万人。
荷兰还受到生活成本危机的严重打击,影响了从医疗保健价格到食品价格的方方面面。
根据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 2022年的一项研究,购买首套房所需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汤姆?“然后你有一个民粹主义者,他说,‘好吧,原因是:寻求庇护者得到优先考虑。“即使这是一个谎言,这就是移民通过种族主义信息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是替罪羊。”
对于欧洲中右和中左的传统政党来说,民粹主义信息的成功带来了挑战。
对付它们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比喻是“卫生警戒线”,即用来阻止传染病传播的保护性屏障。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不与他们结成联盟。
在比利时,这种策略被用来孤立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法国,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党(Front National party)被与之保持距离。
然而,在勒庞女儿马琳的领导下,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集会——不再是贱民。
去年11月,她在一场反对反犹太主义抬头的抗议游行中受到欢迎。这促使批评人士使用了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德语表达——salonf?hig——来形容一个曾经被社会排斥的人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欢迎。
在荷兰,与威尔德斯的政党组成多数联盟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
但随后,欧洲大陆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2015年欧洲的移民危机是极右翼政治的一个契机,此前欧盟对每月约10万名寻求庇护者的到来反应迟缓。
怀尔德斯的反移民言论开始引起更多共鸣。
今年7月,马克·吕特(Mark Rutte)的多数联盟因其对移民问题的处理而瓦解,他的继任者作为自由民主党(VVD)领导人暗示,威尔德斯可能是他再次谈判的伙伴。
“突然之间,投给威尔德斯的一票不再是浪费的一票,”Clingendael智库的科特维格说。
去年12月,威尔德斯所在政党的一名成员成为议会主席,标志着政治接受度的突破。
政治分析人士展望6月份的欧盟议会选举说,荷兰等国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这个拥有4亿5千万人口的欧盟管理机构的一个预兆。
而不是极右翼政党被拉向中间,中间可能转向右。
“这可能是欧洲面临的最大危险,”Clingendael的科特维格表示。——美联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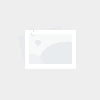

有话要说...